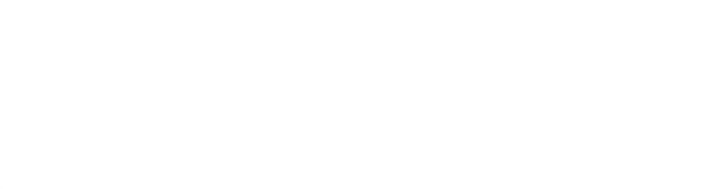- 首页
-
产品中心

三门峡日报“伏牛文苑”(2)
日期:2024-03-10 15:46:03 作者: 贝博ballbet体育最新版/新闻今年6月5日,长期担任同志秘书的张志功同志在与病魔作了艰难的斗争之后,与世长辞,以96岁的高龄,告别了党,告别了祖国,告别了亲人。虽然我也和部分老同志一起向张志功同志治丧委员会发了一封唁电,但是那封简短的唁电实在无法表达我对张志功同志的崇敬、怀念和哀悼之情。他对事业的坚定信念、对党的无限忠诚、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家乡经济建设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注时刻温暖着我的心怀。
张志功出生于1927年11月6日,是三门峡市陕县(现为陕州区)西张村镇凡村人。因为工作关系,我结识了张志功同志,有机会了解到他对陕州、对三门峡的关心和支持。
曾经的陕县电器厂,由于产品不足以满足市场需求,在经济转型初期,陷入关门停业的境况。1979年工厂停产,职工面临着自谋生路的窘境。其间,陕县电器厂发现了一种新型轻质耐火材料新产品——硅酸铝耐火纤维制品。它是一种新型节能环保型新产品,这样的产品发展的潜在能力大、未来市场发展的潜力好,有可能使陕县电器厂“起死回生”。该厂抓住机遇,很快试制出新产品。通过市场调查与研究,该厂了解到,当时的洛阳耐火材料研究所有耐火纤维生产技术,经过申请,陕县人民政府支持10万元,陕县电器厂花费6万元,从洛阳所买回技术,转产耐火纤维。此时,陕县电器厂正处在发展的十字路口,在众多耐火材料生产企业中,一个只有几十名职工的县办地方国营企业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当然,更大的困难还在选准企业走出去的突破口,在当时的情况下,寻求国家主管部门的政策指导和资金支持无疑十分重要。
关键时期,曾任厂供销股副股长的汪建国找到了张志功同志。张志功同志又辗转联系到当时的机械工业部电器工业局。汪建国等同志向机械工业部电器工业局详细汇报了工厂情况,特别是开发耐火纤维节能新产品的前景以及企业在转产后重视管理、狠抓产品质量,工厂生产的“老君炉”牌耐火纤维制品获得全国“新产品研究开发金龙奖”等情况,使国家机械工业部电器工业局对陕县电器厂的工作有了了解和初步信任,随即加大了对该厂的支持力度。此后,陕县电器厂的发展步入快车道。不久,国家确定“六五”期间国家550项重大工程建设项目时,明确了两个“硅酸铝耐火纤维技术引进项目”,分别从美国两家公司引进“甩丝法”“喷吹法”“硅酸铝耐火纤维”成套生产技术,分别拨款100万美元,由首都钢铁公司耐火厂和陕县电器厂承担引进项目的实施。正是这次技术引进,消除了中国与美国在耐火纤维领域40年的技术差距,使中国在这个行业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张志功同志对陕县电器厂的经营管理也关怀备至,比如为企业在北京设立办事处,他亲力亲为,甚至连家乡的出差人员在北京的食宿这类小事,他也不厌其烦地提供帮助。
除了关心陕县电器厂项目,还有陕县化肥厂的千吨尿素项目、陕县龙飞公司的大三元复合肥项目、陕县二仙坡苹果基地项目等,张志功同志也都竭力提供帮助。
张志功同志对家乡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心、支持是全方位的,从政清廉的他把省吃俭用积攒的资金捐出,成立陕县西张村镇凡村助学基金,助学奖优,帮助更多家乡农村学子接受更好教育,还积极筹措资金帮助西张村学校改善办学条件。
张志功同志参加工作前曾就读于豫陕中学,在他的提议和促进下,《豫陕中学回忆录》一书出版面世。
很多熟悉张志功同志的人都说,只要是家乡的人,他不分贫富都会帮助;只要是家乡的事,无论大小,只要他遇到了、知道了,都会尽力提供帮助。
张志功,1927年11月6日出生,河南省陕县西张村镇凡村人。1933年至1939年在陕县西张村镇凡村小学读书。1939年至1944年在陕县张家湾私立豫陕中学读书。
1944年5月初,日本侵略军从山西强渡黄河,入侵陕县。张志功于当年9月逃难西安,在其二哥张志勤租的书店落脚。当年11月,张志勤报上自己的姓名去参加中国青年远征军后,张志功举目无亲,幸遇中学同学杨蔚生(又名杨绒)之父杨子端先生(陕县大营乡辛店村人)在西安经商,并寄居杨家。1945年8月,张志功考入国立西北农学院附属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简称西农附高,校址在陕西省武功县,今杨凌区)。
1948年8月,张志功从西农附高毕业,考入国立西北农学院园艺系。1949年3月,张志功在西北农学院读书时秘密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49年5月在西安参加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北工作委员会工作。1950年3月被选调到中央西北局,给中央西北局书记任秘书。1952年年底,张志功到北京给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做秘书。1955年7月加入中国。1958年4月,张志功随周恩来总理、彭德怀副总理及同志到三门峡参加豫、陕、晋三省领导人工作会议,研究三门峡水库坝高问题。会后,随领导到陕县大营农业社及偃师县岳滩视察农业生产工作。
1978年4月,任广东省委书记,后又兼任广东省长及政委。当年6月,广东省委调张志功给做秘书。继而于1980年11月至1984年5月为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法制委员会主任的做秘书。1981年,张志功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副局级)。
从1950年3月到1964年5月,再从1978年6月到1984年5月,张志功先后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做了20年的秘书。1984年5月,张志功从中央办公厅调任中央统战部办公厅副主任、正局级巡视员,直至1992年5月离休。
离休后,张志功先后参与了《文选》《革命生涯》《传》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著作的编写工作,并在报刊发表了《在习老身边工作20年》及《难忘的20年》等纪念同志的文章。在85岁高龄时,撰写《难忘的二十年——在身边工作的日子里》一书。(摘自党史出版社《陕县党史人物·第一卷》,该文作者南东岳)
感染了新冠病毒之后,我就留下了嗓子沙哑的后遗症,连续两个多月说不出来话。先是到小门诊看医生,又到大医院治疗,均无效果。有人说针灸可以,便怯怯地让中医扎了十天针,虽有缓解,但未痊愈。我心想,下半辈子落了个半语儿,也许是注定的,干脆顺其自然吧。
端午节前回到老家,村里一位长者听我说话嗓音嘶哑,让我泡点金银花喝,还说她当年嗓子哑就是喝了金银花治好的。我问她镇上药店有卖的吗?她说,不用花钱去买,后沟河渠边到处都是。早上起来去采那些带露珠的金银花,药效更好些。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进了沟。这是我最熟悉的山沟,小时候放牛、拽猪草、挖药材、拾柴火,天天都要进沟,一道大沟进去分岔成梨树沟、苇园沟、桑树窊、对门沟、柳树梁、松树壕,闭着眼睛也能叫出这些沟沟岔岔的名。只是四十多年没再进沟里,那些小树变成了大树,羊肠小道也被灌木丛遮住了,还有往日绿树成荫的沟岔口,新增了许多坟墓——哦,我的许多乡亲,在这四十多年间陆陆续续离开了人世,逐渐从村里转移到了这儿。
我往左边一拐,走进了梨树沟。顺着沟渠边往上看,一秧一秧的金银花挂在细树梢上,伸手一拉便到了跟前。这些金银花,有的已经盛开了,有洁白色的,也有金黄色的,像一串串小喇叭在空中摇曳着。我知道,金银花最有药用价值的是花骨朵,开了花的就没有药劲儿了,于是便挑那些发了白的花骨朵往下摘。不一会儿就摘了一塑料袋儿。提着袋子,我并不急着返回,就坐在充满绿意的树丛下歇息起来。刚坐下,突然看见几只鸟儿紧张地往沟里飞去,跟在鸟儿后面的是一个人影,走到跟前才看清,是村里的小当。他扛着锄头,慢吞吞走了过来,见到我有点吃惊,把锄头从肩头上取下,也坐了下来。
小当在沟里种了一些黄花菜,是去锄地的。他告诉我,这些年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沟里很少有人进来。柳树梁上的二十多亩地因怕野猪糟蹋,也撂荒了。过去一到夏天,一茬一茬人进沟采摘金银花,现在金银花的价格涨了几十倍也没有人来摘了。说着,他叹了一口气,也不知是可惜还是感慨别的,老半天没再说话。
“划不来,干一天活收入一百五十块,金银花不压秤,摘一麻袋也不过能干一二斤。”
我知道,现在农村人也像城里人一样,算大账,不愿意干那些费工夫又不赚钱的活儿。秋冬天里,房前屋后的核桃柿子挂满了枝头也没人去收,一问,原来收核桃怕从树上掉下来,收柿子卖不上钱。
下雨了,我们仓皇地往家里跑,小当边跑边说,要是金银花不够喝了,就去来新家的院边摘。
来新和小当都是我小时候的玩伴儿。那时候我们大家一起放牛、拾柴,还一起到山南丹凤七里阴背床板,只是后来各自成家,很少聚在一块了。听说来新儿子、媳妇在苏州打工,来新两口子去豫西大峡谷工地搞装修。前些年,他们在院边种了些金银花,一年能卖两三千元。这几年都不在家,那金银花就自生自灭了。
吃罢晌午饭,雨停了,我漫步到了来新家,打老远就看见院边的梨树、樱桃树上缠着一丛丛金银花。那金银花全部盛开了,倒像是为了美化庄园而专门种下的风景花卉。树下,已经落了一层衰败的花朵,随着微风吹来,空中的金银花还在落雨般纷纷往下掉着。
小当也走了过来,默默地看了良久,说:“金银花一开就不值钱了。”然后再一次叹了口气,也不知是可惜还是感慨别的,老半天没再说话。
两天后,小当给我扛来了一大袋金银花,说是在后沟锄黄花菜时,顺便用镰刀给我割了一袋子。我打开一看,藤藤秧秧的金银花,全是稠密的花骨朵,连一朵盛开的也没有。小当说,你没事了坐在家里慢慢择,准够你喝一年。
小王上班只有两个月,他平时喊老张为张老师,张老师由不习惯到习惯,是呀,以前都是喊师傅,如今的孩子喊老师。老张手把手教小王看仓库的本领,他们相处得很融洽。
其余两间是企业产品的库房,地理位置受限,这里离厂区要有十多里的山路,像大海中孤独的小岛。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风像要撕开小仓库,雷像要劈碎小屋,雨像要下塌小房。小王哆嗦着直往老张身边挪。
“咱们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小仓库,要有足够的胆量才能守好,厂里把这项工作交给我们是对咱们的信任,一定要守好,千万不可出差错。”
“那就好。今晚我得回家一趟,把你婶子要的塑料布送回去把漏雨的房盖住,免得家里又用大盆小盆接水。”
啊,那这小仓库岂不剩下我一个人?小王心里咚咚跳,想求张老师留下。但又想想老张真该回去一趟了,他老伴催了好几次了,可他日夜忙着仓库防雨,修修补补,保住了单位的产品,自己已有半个月没有回家了……小王咬咬牙:“张老师,您走吧,我,我不怕!”
老张点了点头,披上雨衣,夹着塑料布走到门口,又回头说:“你要是实在害怕,就喊出声,也许有人能听见,会给你壮壮胆。”
雨越来越大,风越刮越猛,雷越响越亮,小王守在窗棂下,盼风住,盼雨停,一秒秒,一分分……
小王高声欢呼:“啊,我长大了,我一个人敢守仓库了,而且是在暴风雨之夜。”小王打开房门,跳跃着迎接属于自身个人的第一天。
奔出门,小王愣住了,他不相信自身的眼睛——张老师倚在门框边,呼呼睡得正香,塑料布落在脚下。
“给我点纸,擦板凳。”正准备落座的我,起身找纸。四面八方看遍,没见。问老板,说在桌子上。环顾一圈,依旧没见。“纸贵!”在这空当里,一个老男人粗粝的声音传来,言语间虽然带着戏谑,却一下子让空气里满是尴尬。老板赶紧从案板底下掏出一大卷纸递到我手里。
炒凉粉得一会儿,我们坐等。这会儿,我有机会看清刚才发声的人。他干瘦矮小、六七十岁的样子,一身迷彩工装已经破烂到了“迷彩”的程度,外面套一个棉马甲,质量极差,土落满了每一个针扎过的线圈,有些像砌墙的水泥,灰蒙蒙的难辨原色,头上一顶破落的毛线帽,足可以抖落几斤土。
他的身边坐着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汉子,吸引我的,是他小心翼翼的动作。碗沿上掉落了指甲盖大的一片凉粉,他拿着勺子,笨拙地想把它刮起来,然而凉粉不听话,几乎抹布一般,从碗底儿溜到桌子上,在勺子的“追踪”下,又溜到桌子边儿。最后,还是左手的烧饼帮着勺子,才将那片凉粉送进了嘴里。整一个完整的过程那汉子做得旁若无人,一点儿都没有觉得我在看他。看完这些,我心里有说不清的味道。
这时,一片烙好的白馍片放在碗里,端到同伴面前。二十秒之后,一碗软糯鲜香的凉粉也端了过来。对面老者这时开口了:“女,这是你的馍还是老板的馍?”他这一问,年代感就出来了。当年我奶奶就经常带着自己蒸的馍,出门吃炒凉粉。“老板的。”同伴老老实实回答。“多少钱?”老者问。“不知道呢,还没给人家钱。”她的话音才落,老者说:“不问?不问一片馍给你要一块钱!”言语间大有替我们打抱不平的意思。就是啊,一个馍一块钱,这一片就收一块……老者说完,依旧愤愤不平,又把自己的发现跟中年汉子讲了起来,我不知道他俩啥关系,但从衣着看,好像是一回事。这时大家都看着那片馍,它莫名其妙当了主角。
“老板,给钱!”还是老者,中气十足的声音,苍老而不失豪迈。只见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把人民币。好久没见过这么多钱了。说钱多,是因为“品种”多,十元,五元,一元,最大面值是二十元吧。他仔细地数出几张,问价,两碗凉粉十二块。他把钱递出去。老板随手一接,大声喊:“找八块!”老者哈哈一笑,说:“小子啊,我给你的是十五块,你找我八块干啥?找三块就够我的了。”听到这里,我抬起了头,认认真真看了看老者,还是土马甲,还是破烂的迷彩服,还是能抖几斤土的帽子,还是一脸调侃神情,却莫名好看了许多。他果然还是絮叨多话的:“恁冷的天,你找我八块!都这样找,你挣啥?锅该漏了!”年轻的老板很感激,一迭声地说谢谢。老者依旧教育他,老板也继续一迭声地谢。虽然我知道,八块钱对这个生意火爆的老板来说算不得什么,但老者明显很享受“小子”的感谢。而我,不但享受“小子”的感谢,也很享受“灰尘老者”的“痞帅”。看着他带着木讷的中年汉子走远,一副豪迈自信的神态,我的心里居然莫名舒畅。
凉粉摊上风波的旁观者,是我和同伴。她从碗里抬起头,说:“这个值得写。”是的,这个值得写,我也觉得!
六月,草木葳蕤,石榴花渐次开放,连不谙世事的野枣花也不甘寂寞地把盈盈笑意挂在枝头。
微雨,轻晨。卢氏豫西大峡谷近百亩油菜花掀开面纱羞羞答答地立于小路边、山溪旁,含情脉脉地注视着撑着伞慢慢赏花的人群。
野豌豆揣着鼓鼓囊囊的豆荚,把一串串绿色的梦挂在藤蔓间,只等一声嘹亮的金色号角,就向着那幸福出发。
擎着蓝色华盖的矢车菊,此刻正星星点点地散落在田垄上、小路旁,期待着与疲惫的灵魂来一次最美的遇见。
那一望无际的油菜花,用一地耀眼的黄诉说着粗心的画师在人间的遗忘。一朵朵、一簇簇似一个金色的童话在世间的演绎。从南到北,从西到东,一片黄又一片黄,那是油菜花放飞的幸福期望。
泥墙根,一场花事正在孕育,挺着大肚子的月季花正靠墙待产。狗尾巴草恣意地生长,晶莹的小水珠在它们狭长的叶子上打着旋儿,惹得这些狗尾巴草不胜其扰地左右摇摆,大喊“痒!痒!”枫树绿色的小爪子,因季节的电量不充足,还来不及闪光。
千年银杏树用它们的沉默不语向世人暗示着长寿的基因密码。关帝庙上的五脊六兽记录着人们对忠诚和信义的膜拜。
汽车在雨后的公路上逶迤而行,黛色的起伏的连山仿佛踊跃的铁的兽脊,远远向车尾跑去了。及至山巅,但见远山的褶皱里雾气升腾,一会儿变幻作一匹四蹄生风的白马,一会儿又像一座漂浮着的冰山。转眼间波涛翻滚,秀岭没于云海之上,变成云海中的一座小岛。
微雨的黄昏,我垂首在大淙庙寂寂的大殿前。双手合十,把虔诚写在脸上,把希冀注入血脉。对生老病死的无力,对爱恨情仇的无奈,在这里寻一个出口,抚慰发烫的伤口,把苍白的灵魂超度。
庙门前野豌豆疯长,含一粒入口慢慢咀嚼,细细品味大淙的传说,那关于爱情的坚贞、亲情的守望、信念的坚守都是人类最朴素的理想。
有悦耳的歌声传来:“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座座白云绕山间,一片片梯田一层层绿,一阵阵歌声随风传……”短暂的沉默后,同行的伙伴会心一笑,同山那边的歌声和起来。峡谷中久久回荡着妙曼的音符。
小溪、竹林、石板路,一座院落一首诗;茶室、酒肆、图书角,一方天地一卷画;泥巴墙、木隔窗、大露台,让人忍不住想夜宿于此,体验山村夜凉如水,繁星满天的唯美浪漫。
古有“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之说。我深以为然。大概高层次的隐逸生活,便是在都市繁华中守一份心灵宁静吧。